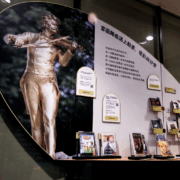偏激時代來臨——是公共對話,還是惡意開罵?國家兩廳院攜手《報導者》,探索情緒與真相的邊界

在這個分化的時代,我們是否還能好好對話?
當理性語言被情緒淹沒,劇場與媒體能否重新打開理解的縫隙?
文|倪暐
圖|林韶安
時序流轉,秋意盎然。國家兩廳院一年一度的「秋天藝術節」正式開展。這項自2021年起以策展形式推動、聚焦多元當代議題的藝術節,今年主題為「在裂縫中重組我們」,匯集來自臺灣、希臘、比利時與韓國的七檔節目,共二十一場演出,透過當代劇場回應斷裂的現實,召喚集體感知的共鳴場域。
藝術節並舉辦三十六場周邊活動,包含節目導讀、工作坊、講座與創作者對談,同步推出Podcast節目《好哲凳》,將聲音帶出劇場,延伸思考的可能,邀請觀眾「穿越裂縫」,尋找理解與想像的下一步。
今年,秋天藝術節首度與適逢十週年的獨立媒體《報導者》合作,以「如何開啟對話?」為主題推出多項系列活動。《報導者》十年來累積超過五千篇深度報導,持續挖掘現場真相,提供多元觀點,開拓讀者的思考視野。該媒體亦推出Podcast節目《The Real Story》,透過關鍵當事人現身說法,讓聽眾用耳朵走進採訪現場,聽見記者的發現、幕後的故事與人物生命。
在這樣的契機下,兩廳院與《報導者》共同策劃Live Podcast現場對談——「偏激時代來臨:是公共對話,還是惡意開罵?」。當媒體越來越分化、立場越趨極端、公共討論空間緊繃之際,活動邀請觀眾與讀者走入現場,參與提問與對談,嘗試從思辨中汲取力量。

兩廳院與《報導者》共同策劃Live Podcast現場對談——「偏激時代來臨:是公共對話,還是惡意開罵?」,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劉文指出,「分化(differentiation)」在民主社會中原為常態現象,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意見與立場。(林韶安攝)
分化與極化的社會
這場節目邀請國家兩廳院藝術總監劉怡汝、《好哲凳》主持人劉文以及《報導者》營運長李雪莉三人對談。其中劉怡汝於任內開啟以議題為策展核心的「秋天藝術節」,並實踐「永續」與「共融」價值;李雪莉則是新聞資歷豐富、屢獲殊榮的媒體人;劉文為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,長期關注全球性別與種族運動,同時為《好哲凳》第五季主持人。
現場亦開放提問,讓不同立場與觀點的人能進行交流,使思辨成為日常,讓尊重與理解成為社會進步的基礎。
劉文指出,「偏激時代來臨」的主題源於社會心理學的觀察——「分化(differentiation)」在民主社會中原為常態現象,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意見與立場。
但當「分化」走向「極化(radicalization)」時,情況便不同。「如今許多老牌民主國家,尤其是美國,出現越來越多政治暴力事件。這是否意味著人們覺得,意識形態的不同無法透過民主機制解決,而必須用極端手段去矯正對方?」劉文表示,這也是媒體人在當代不得不面對的課題——如何分辨公共對話與惡意開打的界線?

兩廳院與《報導者》共同策劃Live Podcast現場對談——「偏激時代來臨:是公共對話,還是惡意開罵?」,《報導者》營運長李雪莉表示,科技與社群演算法讓人們被困在自己的同溫層,只聽到想聽的聲音。(林韶安攝)
李雪莉以自身經驗回應。她說:「我的工作之一,是巡視社群留言與輿論動向。但現在的對話,往往不再是真正的『對話』,而是『開戰』。」她表示台灣雖自豪為多元社會,但如今的狀態更像是「分裂」。「多元(diversity)」與「分裂(division)」其實同源於字根 di-,意為「分開」。多元是建立在共識與共同價值之上,能包容差異;分裂則是將整體切割為敵對的部分。
李雪莉認為,從多元走向分裂的原因主要有三:第一是科技與社群的「裂解效應」,演算法讓人們被困在自己的同溫層,只聽到想聽的聲音;第二是媒體功能弱化,新聞從「探索事實」變成「追貼文」;第三是「新聞的被動消失」。根據英國牛津大學路透新聞研究中心研究,從2015到2024年,年輕人主動避開新聞的比例急遽上升,連55歲以上族群也開始不看新聞,因為「太讓人不快樂」。她補充,Meta平台上新聞內容從2021年的12%降至2025年的2%,「我們幾乎看不到專業新聞內容,社會於是變成情緒多、事實少;娛樂多、理解少。」
劉文補充,在分化時代,「多元」的背面其實就是「碎片化」——從過去「老三台」時代的單一資訊,到今日無限選擇,卻也更容易只接觸自己立場的觀點。

兩廳院與《報導者》共同策劃Live Podcast現場對談——「偏激時代來臨:是公共對話,還是惡意開罵?」國家兩廳院藝術總監劉怡汝表示劇場能提供的,是多樣的真相。(林韶安攝)
劇場裡的真相與共鳴
劉怡汝認為,「多元」是一種稀有的美德。人們太容易只相信自己想相信的,而劇場提供的,是多樣的真相。「劇場是呈現真相的場域。很多在社會上難以看見的事,藝術家往往能感受到,並轉化成作品。」她說,劇場最大的特質是「現場性」——觀眾在兩三小時的演出與座談中,能慢慢體會藝術家的思考。「或許不會改變想法,但會意識到『原來還可以這樣想』,這就是劇場的社會角色。」
打開視野 進入盲區
劉文分享,兩極化(polarization)現象自1990年代後成為政治學熱門研究。以美國為例,1994年前,多數共和黨與民主黨選民會在不同時期支持不同政黨;然而到了2010年代,這種「搖擺」幾乎消失。1994年共和黨中有65%的人持自由派想法,到了2014年僅剩12%,變化驚人。「反觀台灣,搖擺選民仍有四成,顯示我們的極化程度尚未失衡。」
李雪莉補充,《報導者》創立十年間,前五年台灣言論市場尚稱理性,但疫情後明顯激化。「以前留言雖有批評,但多半想講道理;如今更多是叫囂與貼標籤。」她指出,許多帳號並非真實個人——有的是假帳號、無互動帳號,或只轉發政治貼文。「這些匿名者在沒有責任的情況下可以隨意辱罵,而我們卻必須在透明與可追責的制度下對話,這是當前言論市場最不對等的地方。」
劉文表示,資訊爆炸並未帶來理性,反而讓人更難溝通。人們在認知上分裂到連「什麼是事實」都無共識。焦慮外溢,導致群體更緊抱自我認同。「越無法掌控外部世界,就越想待在熟悉的小圈圈。」

兩廳院與《報導者》共同策劃Live Podcast現場對談——「偏激時代來臨:是公共對話,還是惡意開罵?」,媒體、場館、學者與民眾齊聚一堂,反思公共對話的能與不能。(林韶安攝)
理性之前 先有同理
在網路時代,公共討論與個人情緒的界線幾乎消失。「一個留言者可能只是想抒發情緒,但對被留言的人來說,那是具體攻擊。」劉文說,當防禦機制越強,人就越難聽見他人。李雪莉補充:「同一篇報導,不同立場讀者能讀出相反結論。這不是誤解,而是人們以情緒理解世界。」她強調,理性討論的起點必須是「同理」,「沒有願意理解彼此情緒的基礎,理性語言便成了一堵牆。」
劉文亦指出,現今社會最缺乏的不是資訊,而是信任。人們懷疑每一個帳號是否真實、是否有立場、是否為側翼。「當信任稀缺,我們就只能相信與自己相似的人,結果更加分裂。」
李雪莉認為,真正的理性討論或許難在網路上發生,但「在現場,它就有機會。」「報導讓我們看到問題,對話才讓我們重新相信彼此。」她說。

兩廳院藝術總監劉怡汝(圖中者)表示,藝術也許不能改變社會,但能讓人暫時放下防備,互相傾聽。(林韶安攝)
劇場 讓對話重新開始
劉怡汝認為,劇場正是社會的縮影,能讓不同背景、年齡、身分的人共享當下。然而近年「共同經驗」愈發難建立。「以往人們認為藝術是值得理解與體驗的,如今我們必須更積極邀請、解釋、讓更多人理解為何要進劇場。」她說。
兩廳院近年致力於創造「場域」——一個讓人能看到不同觀點、甚至「不認同」的場域。「因為藝術不是要提供標準答案,而是提供不同問題。」
在不被攻擊與真誠對話間找平衡
「藝術能改變社會嗎?」劉怡汝問。她回答:「也許不能立刻改變,但能讓人暫時放下防備。」觀眾走進劇場,看的是故事,也是看見別人的人生。兩廳院多年舉辦聚焦性別暴力、移工、環境、城鄉差距等議題的節目,「只要觀眾願意進場,那個『願意』本身,就是開始。」她相信,劇場的角色是創造空間,讓人能彼此聆聽。
劉文說,在這個節奏飛快的時代,媒體、劇場與學術其實都在對抗那個「快」。
「唯有慢下來,才有理解的機會。」李雪莉補充:「在分化的時代,我們要有勇氣去聽見彼此的不舒服。」劉怡汝則微笑說:「歡迎走進劇場,劇場讓人重新學會共處。」

兩廳院與《報導者》共同策劃Live Podcast現場對談——「偏激時代來臨:是公共對話,還是惡意開罵?」,展現理性對話。(林韶安攝)
媒體人的心防與修復
現場民眾提問,如今偏激言論充斥社群媒體,媒體人如何調適心情、維護身心健康?李雪莉表示,新聞媒體與自媒體最大的不同,在於責任與風險管理。「新聞媒體必須在法律基礎上發言,不得使用煽動性標題或簡化內容,必須保有脈絡。」
《報導者》原則是若記者被點名,李雪莉說不會讓記者或當事人單獨面對輿論壓力,而由編輯台統一回覆,並由社群、編輯、核稿人共同討論應對。她也透露,《報導者》與診所身心科簽約,提供長期關注戰爭、性別暴力等議題記者心理支持,並提醒同事不要在政治議題下留言或按讚,以免被追蹤,「這是我們保護同事的方式。」
情緒能推動議題嗎?
現場亦有民眾提問:情緒化言論是否有助議題推進?劉文認為「答案是肯定的」。她舉MeToo運動為例:「那些被指為不理性的文字,其實是創傷經驗的真實呈現。」劉文舉例,在社會中,女性用情緒說話常被質疑不可信,「這本身就是不平等。」她分享從歷史看,法律與社會運動的推進,背後都有情緒與故事,「關鍵在於我們對話的目的,是策略,還是理解?先理解情緒,再處理議題,才是前進的關鍵。」

兩廳院與《報導者》共同策劃Live Podcast現場對談——「偏激時代來臨:是公共對話,還是惡意開罵?」,現場民眾提問熱烈。(林韶安攝)
劇場的打開與分眾挑戰
也有民眾問,面對媒體分眾化挑戰,兩廳院如何兼顧普及?劉怡汝表示,兩廳院有一半經費來自政府,「我們不能選擇性服務,沒有只為特定族群存在的理由。」她指出,每年約有六十萬人次走進兩廳院,希望能提升至百萬人次。「以往報紙媒體有『魔幻子彈效應』,但如今已不可能,我們更要靠內容多元吸引觀眾。」
她分享:「春天有『台灣國際藝術節』,主題『繁華盛開』;『新點子實驗場』前衛挑戰視覺;『秋天藝術節』聚焦社會議題;『兩廳院夏日爵士』則延續二十年傳統,邀請國內外頂尖樂手。歡迎大家走進劇場,買票支持。」
值得一提的是,在這場對談中,兩廳院特別為聽障者安排即時聽打字幕服務,透過即時轉譯文字與符號,讓聽障觀眾也能同步參與,盡可能降低溝通障礙。「我們的目的,就是讓更多人能走進劇場,不受任何限制。」劉怡汝說,「努力降低所有障礙,讓每個人都能接近表演藝術。」

兩廳院與《報導者》共同策劃Live Podcast現場對談「偏激時代來臨:是公共對話,還是惡意開罵?」,期待人們「慢」下來,彼此聆聽互相理解。(林韶安攝)
在這個分裂與喧嘩的時代,兩廳院與《報導者》嘗試用對話、用劇場、用真誠的傾聽,修補裂縫。
或許,面對偏激,我們不必急於辯贏;只要願意彼此聽見,就已經是一種開始。